-
高三的教学楼,像一台精密而冷酷的机器,我们是被设定好程序的零件,在课桌、食堂、宿舍三点构成的轨道上高速运转,目标明确,却也沉闷得令人窒息。我的世界里,只有倒计时牌上不断减少的数字,和试卷上那片需要反复攻克的红色领地。
直到,我遇见了它。
那是一个疲惫的晚自习后,我在教学楼后墙的角落里,发现了一双亮得惊人的眼睛。那是一只猫,一只极其普通的橘猫,瘦,但不算孱弱。它就蹲在垃圾桶的阴影里,安静地看着我,眼神里没有讨好,也没有恐惧,只有一种纯粹的、野性的审视。我与它,在清冷的月光下,进行了长达十几秒的对峙。最终,我挪开目光,继续走我的路。它则轻盈地一跃,消失在黑暗中。
那就是我和它的开始。没有温情,只有一次彼此打量。
后来,我几乎每天都能在那个角落看到它。它像一个沉默的哨兵,守着它的领地。我偶尔会剩下半个包子或一点火腿肠,放在固定的地方,然后走开。它从不当场吃,总要等我走远了,才踱步过来,迅速叼走。我们之间,形成了一种古怪的、不言自明的默契——我不试图靠近,它不给予感激。
我给它起了个名字,叫“坐标系”。因为它总喜欢蹲在墙根那块破碎的棋盘格地砖上,像一个被随意标注在坐标图上的点。这个名字,很理科,很符合我当时的状态。
我与坐标系的“交流”,仅限于此。它从不发出呼噜声,我也从不试图抚摸它。但在无数个被难题逼到墙角、被压力挤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刻,我会下意识地走到那个窗边,向下望去。十有八九,它都在那里,不是在晒太阳,就是在慢条斯理地舔舐自己的皮毛。它那种全然活在当下、专注于自身的样子,有一种奇特的镇定效果。我看着它,仿佛能从它那里借来一丝不为外物所动的从容。
有一次,模拟考惨败,我情绪低落到极点。晚上,我又去了老地方。它不在。一种莫名的失落裹挟了我。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,感觉自己像一个被遗弃的零件。不知过了多久,我感觉到一道视线。一抬头,它不知何时回来了,就蹲在离我不到两米的矮墙上,静静地看着我。月光勾勒出它瘦削的轮廓,那双绿色的眼睛,像两潭深不见底的古井。
那一刻,我没有说话,它也没有动。我们只是隔着一段距离,互相望着。但它无声的陪伴,像一种无声的理解,缓缓注入我干涸的心田。我忽然觉得,那些分数和排名,在生命本身的坚韧面前,似乎轻了许多。它一无所有,流浪求生,却依旧保持着它的尊严与节奏。而我,拥有这么多,为何要被一次失败击垮?
从那以后,我和坐标系的关系依旧疏离。我投喂,它接受,仅此而已。但我心里明白,它是我那段灰白岁月里,一个无声的盟友。
高考前夜,我把我所有的零食库存都带给了它。它破天荒地没有立刻离开,而是蹲在原地,看着我。我朝它挥了挥手,轻声说:“再见,坐标系。”
它最终转身,像以往无数次那样,融入了夜色。
我如愿考上了远方的大学。离开家乡前,我特意去那个角落看过,它已经不在了。或许找到了新的领地,或许开始了新的流浪。
如今,我已坐在大学的图书馆里。偶尔,当学习的压力再次袭来时,我还会想起它,想起那只名叫坐标系的流浪猫。它没有教会我任何具体的知识,却用它整个的存在,给我上了一堂关于“自我”的课。
它是我按图索骥的青春里,一个不期而至的、自由的坐标。我们短暂交汇,然后各自远行。它提醒我,在追求世俗定义的“终点”时,永远不要丢失那个像它一样,能够安静独处、凝视自身、在哪怕最逼仄的角落也能活出自我的灵魂。
我和它,一个是困于题海的少年,一个是游荡街头的生灵。我们是彼此生命的过客,却也是对方世界里,一枚沉默而重要的烙印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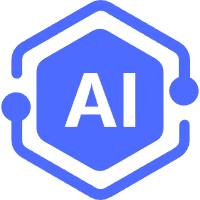


期待多多更新